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一: 爱情中的人性
正如高晓松所言互联网让一切公开化,所有人性不堪的一面全部暴露出来,时下明星出轨的事屡屡曝光,这不是世态越来越不堪,只是人性真实的一面在互联网下藏不住。于是,当事人血淋淋的伤口被暴露于阳光下当做大戏上演,众多看客纷纷站队痛骂负心人彰显自己高尚的道德观。
可是,有多少人真正追问过是谁导演了这些大戏呢?残忍的狗仔队为了博眼球,表面上在做道德监督,其实干的都是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的事,但他们只是编辑,当事人也只是演员,总导演只有一个,就是根深蒂固的人性,人性不变,所以大戏不断。

《物演通论》中说“人性是物性的绽放”,身为人,自然的求存状态就决定了人性中不可磨灭的贪嗔痴。自然物质演化是个分化过程,最后衍的人类需要最多的依存条件。越来越多的物质依存需要让我们追求事业,自然赋予的繁衍本能让我们追求爱情。我们以为我们生而自由,实际上永远都被编织在人性贪嗔痴的罗网中。对于精神层面高一点的人来说,看破名利容易,而世人也不会讴歌名利。但爱情却是人类从诗歌诞生就被永恒赞美的呀!《物演通论》第三十一章如此深刻的戏谑诗歌:
所谓“诗意”,其实就是至弱者对其弱性的无意识抒怀,乐其为弱性所成就,并继续有所成就;悲其为弱性所困扰,且无法克服此困扰。
爱情只是人类至弱人性中的一项,以爱情解读此段如下:无数的诗歌赞美爱情,却不知爱情只是人性无数贪嗔痴中的至弱一环,我们以为爱情能带给我们幸福,并为爱情用婚姻圈下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誓言;却不知从爱情中得到的幸福总会用等量的痛苦偿还,爱情的本质就是喜新厌旧或者说发展变化,一生一世一心一意注定是越来越难圆的梦幻。
何为爱情?说到底爱情无非是在孤雌繁衍变为两性繁殖的体质分化中,性分裂导致的两性对媾合归一的最本能最原始的渴望,这也是大自然赋予的物种求存的规定:也就是说,性爱是最本能的爱情,也是动物式的爱情。而动物性本就是最深层的人性。但人作为智化动物,为了求存,不仅需要感性、知性,更进一步代偿出理性,其个体的不同越来越表现为智质(即认知即灵魂)的不同,即人与人最大的区别是世界观价值观的区别。对动物而言,爱情的选择主要在于的性能力的体质差别,这种差别是有限的,所以此阶段的两性匹配很容易;而随着智质分化的越来越严重,价值观会越来越多元,自然匹配越来越不容易。这也是人类择偶可选择对象越来越多,爱情却越来越难的原因。年轻人因为荷尔蒙的助力会稍微容易些,但灵魂的匹配不足却会随着荷尔蒙助力的消失后没法继续。最重要的是,灵魂或者说人的认知是不断变化的,两个人变化的方向或者变化的程度不匹配,也必然很难始终同行。也就是说,在社会文明化加速的进程中,爱情的发生和维持都越来越难,这也是整个社会结构越来越不稳定在爱情侧面的表达。统计数据也显示文明进程与离婚率成正比,以至于有人甚至认为离婚率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一言以概之,对人而言,爱情就是两个人灵与肉的匹配。纯粹的爱情和利益无关。徐志摩致力于追寻“灵魂伴侣”,但如果林徽因和陆小曼换一副丑陋皮囊,就算才情再翻一倍,怕也是未必是其追寻对象。只有灵魂匹配是最深的挚友,只有肉体匹配是最好的炮友。年轻时,荷尔蒙泛滥,肉体匹配的需求更高,灵魂次之;年龄越大,灵魂的匹配要求越高。有才情气质才能欣赏流韵风骨,有俯察天地的眼界才能见悲天悯人的胸怀。但灵性的高贵永远只是理性的胜利,却不是真正人性的彰显,真正人性中感性、知性、理性从来一体贯通,并无可分。辩机和尚和高阳公主的爱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佛理对人性再透彻的辩机还是会让佛学赋予的灵魂输给青春下的肉体,让无比清明的理性输给至真至纯的感性,因为无论感性还是理性,都是自然求存代偿下赋予的人性,理性抑制感性,而感性沉淀在人性最深层,拥有更强大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力量。从古生代寒武纪前后“性分裂”到今天,性爱的基因沉淀了5.4亿年,而高贵的理性从灵长目开始出现到现在不过五六千年。所以《物演通论》一百二十七章指出: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的临床方法发现,无论人类的社会精神现象何其夺目,决定着人的智性行为的基本原因却是最为人类不堪启齿的“性”的潜流,或者还有一点儿对“伟大”的趋求。弗氏的学说很有些幽默,他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指明了繁华人性的归宿,使人类回落到原始生物唯求生存的基点上,这个生存的基点恰恰对生命提出了两项要求,即借助“遗传”以对抗残弱——“性”的渴望(“本我”之要素);和借助“变异”以超越残弱——“伟大”的渴望(“超我”之体现)。
也就是说:性爱彰显的“本我”不过就是人性中最深的动物性的源流,是爱情最深层的潜意识本能;智质分化彰显的“超我”表达着智质急剧分化的个体所拥有的同步增长的意志,渴望以自我分化实现社会的整体价值来完成自我的最大价值,在爱情中直接表现为价值观的耦合或匹配,并视彼此为一个整体。总之,从肉体到精神,从本能到灵魂,一方面表达着“本我”不可撼动的体质媾合本能,一方面表达着“超我”越来越缥缈的智质构合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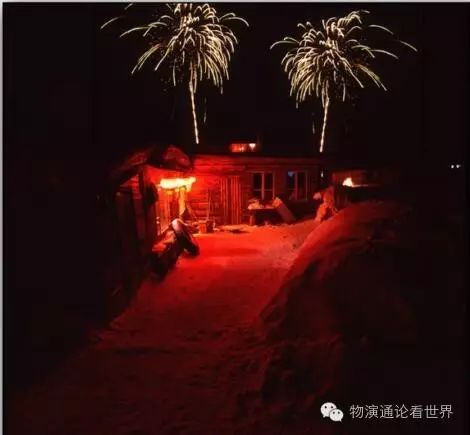
最早的氏族社会是群婚制,一到晚上,本氏族的男性都会到另一个相邻氏族中去媾合,白天各自回家,是为两合氏族,因此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在母系社会中生养。这时候的两性关系最符合人性本能,和动物社会相对接近。对偶婚制是私有制出现的产物,为了明确孩子的财产继承权大社会分化为小家庭,两性关系才开始变化。社会的变化决定了爱情观的不同。但私有制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氏族社会长达百万年,爱情观为了社会稳定求存而不断变化,百万年社会铸就的两性关系下的人性本能,包括5.4亿年沉淀的性爱本能却是始终不变的。所以,就算会被“浸猪笼”,总还是有那些痴男怨女上演悲情的故事;就算被千夫所指,婚外情的故事从不会断。
道德、婚姻归根到底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结构的产物,并不是爱情和人性需要的结果。明眼人都明白当下的道德在许多年前或许多年后都是个笑话,可是谁能活在多年以前或多年以后呢?当下存在的,就是当下合理的,有其社会功用。既然入了红尘罗网,哪怕仅仅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免于彼此伤害也应该恪守道德。我们入乡随俗,未必是基于对当地风俗的认可,而是尊重乡人的价值观,不伤害乡人的感情。所以,表面上我们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实际上我们既被身囚,又被心囚,还被社会结构所囚。人性本身并无善恶、并无美好与丑陋,只是纳入社会结构,便有了道德评价;而不同的生存境况,也决定了善恶的方向。

文明社会,从识字开始,我们读的就是“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诗篇,听的就是梁祝化蝶的音乐和传说,文青心里的爱情从此就该是那个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唯美模样,可真实的爱情样貌总难唯美更不完美。若视纯粹而完美的爱情为信仰,爱情终会变成自戕的利刃。所以,《魂断蓝桥》里的玛拉遇不到罗伊也许还能活,遇到罗伊只能死;杜十娘错误编织了爱情的梦想,只能和百宝箱一起沉江;而尤三姐自刎所捍卫的尊严和试图用生命证明的不过是心中赋予的爱情的完美模样和神性光芒。
对完美爱情的追求是最大的贪嗔痴。所谓完美的爱情,就是彼此完整的自得与自失:因为全身心的付出,便忍受不了一丝丝细节上对方的不在乎;以为得到对方的全部,就当不起得而复失。于是,当下的完美铸就一生一世的贪。而贪不得时,由爱而恨化为最深的嗔。至于象梁祝与罗密欧朱丽叶那样可以放弃生命是最执念的痴。爱情中的所有伤害皆源于此。在爱情中,谁不是卑微到尘埃里?谁不是待宰的羔羊?爱情本身就是天堂或地狱,谁有的选?爱之极,伤之极。以爱情为信仰,必以生命殉爱情。
所以,看破名利容易,看破纯粹与完美难呀,小人以身殉利固然本末倒置,贤人以身殉名、圣人以身殉天下在庄子眼中都是并无二致的“以物易其性”。任何时候以身殉爱情同样是“以人性殉神性”的执迷。泰戈尔说:“我不愿意做权力的轮子,我只愿做被压在下面的活人之一”。我想说:永远不要去追求神性,请真实的做个俗人之一。烦恼即菩提。没有烦恼当前的,也用不着追求菩提境界。所谓神性,不过就是苦难历尽或繁华阅尽后,在认知上对天地人生的深刻理解,并因此而通达和悲悯。必须做神的,多半是对于完美或圆满贪嗔痴到极致,知其不可得而无求。所谓圆满态,也是一种适应态,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就是打破适应态,以避免无求的无聊。精进修行以求涅槃,心心念念普度众生,何尝不是更大的我执。
我们自然的本性从来就不完美不高贵,只是我们的理性为我们缔造了各种高贵的超越生命的意义——实际是为达成社会整体求存规定的个体服从整体的自我牺牲——包括忠贞的唯美的永恒的爱情。王宝钏就是这种爱情观最典型的牺牲品。用一生殉一份情,最后18天真的幸福吗?以生命的所谓意义殉生命本身真的高贵吗?归根到底,生命没有所谓意义。意义这个概念自产生起就是别有用心的,是扭曲生命的借口和幌子。说不好听是政治统治的文化手段,说好听是社会求存的自然要求,无论如何,作为整体中的每个个体必须明白,社会的所有追求归根到底应该是为众生能更好的活着,而你本就是众生之一,好好活着,不伤害别人也别伤害自己,活着是唯一的信仰。人人都能好好活着,根本就不需要谁来做圣人殉天下了!
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爱情的永恒要么是彼此囚在原地,要么是彼此共同成长。爱情的来去得失和生命的变化乃至生死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顺应自然就好。王尔德说:“如果你有敌人,那么对敌人最好的报复,就是你快乐的活着!”这层境界,这层报复,自然比用伤害对方的方式好;但更高的境界是:我们根本无需报复,没有执着就没有伤害,没有争夺就没有敌人,我们快乐的活着,不该为别的,只为珍惜和尊重自己的生命本身。生命如花,只需绽放:所有的经历、所有生命中逝去的日子都是生命的落叶,零落中化作春泥,滋养我们全新的生命。请修炼我们的身体,使其更美好更健康;请修炼我们的心灵,使其更深刻更博大;请修炼我们的灵魂,使其更高贵更宽容。身心灵的成长让简单自然的快乐如雏菊开遍山野每个角落,爱如淡淡的花香弥散天地间。

【结语】
谨以此篇献给所有在爱情中挣扎的灵魂!还原爱情的真实面目,以安抚所有人性或爱情罗网中脆弱的灵魂。希望所有受伤的灵魂都能真正放下而自在快乐,希望不要有太过执迷的灵魂让爱情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王东岳先生说“冷眼旁观是最大的快乐”,是极深刻的见地!真正能冷眼旁观看透天地世事的人、能明了人性悲天悯人的人,必有强大的理性智慧,亦有丰富的感性灵魂。没有红尘中颠沛跌宕的苦难,哪有觉悟后冷眼旁观的超然。其实无论哪里都是红尘,心念不同,一念便是一重天。
没有燃烧过的生命总渴望激情的浓烈,燃烧过的人只想淡泊的冷眼旁观。总是要把寂寞坐断,才能重获灵魂的自在与安然;总是要把泪水倾尽,才能灌溉出笑容的坚强与灿烂;总是要反反复复追问所有苦难的发端、爱情的渊源,才能彻底明了天道演绎下至弱的人性,才会理解“众生皆苦”,才能去真正理解所有在爱情中无奈而卑微的脆弱灵魂。这就是见自己(反思自己的脆弱与来由)、见天地(明了人性的至弱与来由)、见众生(理解众生的脆弱与来由)的成长之路!

真正的强大,永远不是把别人踩在脚下,而是能从每个不同的角度,理解每一个人。永远不要肤浅的用道德去随意评判别人,更多的站在别人角度想想为什么更有助于理解人性,每个人的先天基因、出生背景、后天教育、个人经历、价值观等都不同,是非对错往往只是你站的角度决定的;就算是十恶不赦的人,你换个角度只要想一想,需要经历怎样的家庭、社会环境和经历,才能变得十恶不赦,哀叹之余,怕也会有更多的思考。唯有思考和理解,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