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二:浅谈神智学与身心灵
鲁道夫·施泰纳的《神智学》因为很接近东方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很接近一元论的东方哲学如道家佛教的思想,所以很容易被国人接受,以致于由此种理论应运而生的华德福教育在国内颇有市场。这种贴近自然态、疏离于文明态的生存方式对个人灵魂的塑造无疑更自然、更完整、更健康,但陶渊明的桃花源真的存在吗?你真的可以完全置身于社会文明体系的覆盖之外吗?当整个人类的大灾难濒临之际,如核冬天、如全球性的大瘟疫等,你真的就能幸免?每个个体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一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覆巢之下无完卵,整体覆灭之际,个体的存活几率微乎其微。所以,我们不必等到人类系统危机整体爆发的时候才被迫以人类整体为视角处理问题,而是在当下,就应该学会以这样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就好比军阀混战对中国百害无利,只有外国入侵才能众志成城,但如果更早的时候军阀就能在更高的理念上达成统一而建设这个国家,国家也不会弱到被入侵。小到企业、大到人类,莫不如此,就看你的认知格局了。当然还有更大的视角即整个存在的视角,也唯有在这个视角上我们才能明白人类应该如何更稳妥的求存,其中也包含了对整体存在的维护,如对环境的维护就是对人类的呵护。
鲁道夫·施泰纳作为奥地利的社会哲学家仅仅是广义的哲学家,实际上其理论离狭义哲学很远,所以在哲学史上也没有位置。鲁道夫·施泰纳的《神智学》,包括密契主义,其实都是一种延续前神学或神学文化的粗陋的世界观模型,这种粗陋源于对当下大量新信息或者说科学知识的无知,而一旦我们有了更多更新的信息量以及新的更大更精致的涵盖最新信息量的逻辑模型(科学都是建构一个新的逻辑模型,经过实验观察验证后成为新知),旧的粗陋模型中的错误便显而易见了。比如《神智学》中对身心灵的解读就是对当代人体神经学逻辑学等精神本身的无知,所以无法真正做到对身、心、灵的深刻反思(即纯逻辑或纯理性的反思),更多的还是出于朦胧的知性、理性混合的感知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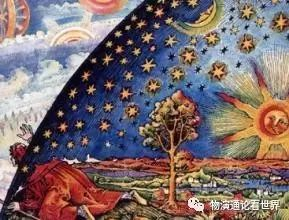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说身心灵,何为身心灵呢?鲁道夫·施泰纳的《神智学》中这样表示:
身指的是,人周遭环境中的事物是透过它来呈现,如同前面所提到的草地上的花朵。心这个词所意指的是,人如何透过它而将事物与自己的存在联系在一起,透过它而感受到对事物的有趣或无趣、喜欢或不喜欢、快乐或痛苦。灵指的是,当人以,依歌德的表词所说,“近乎神性的本质”细察事物时在他身上启示的东西。——在此意义上人是由身、心与灵所组成。
人类仰望布满繁星的宇宙:心所体验到的悸动是属于人的;而人在思维、在灵中所掌握的星辰永恒法则并不属于人,而是归属于星辰本身的。
因此人是三重世界的公民。人透过其身而归属于一个也是要透过身才能够知觉到的世界,人透过其心建构出其自己的世界;而另一个超越其他两个的世界,则透过灵本身启示给人。
简而言之,《神智学》中的身就是能感受外界的肉身,心是对外界的感受本身,灵是对事物的极致的认知(有点类似儒家的格物致知),只是灵所揭示的是客观世界的规律。
但实际上这样的认识在康德以前还可以理解,在康德以后就太落后了,因为康德的先验论已经确定了人的经验是先验直观感受的结果,人的知识是先验综合判断的结果,所谓灵,就是对这个世界显意识层面的本质认知(即理性抽象的最高结果),也包括此显意识成为确认认知后沉淀为我们潜意识的一个结果,所以它也不可能客观,只能是主观的。人没有真空的感知通道直达客观世界(即康德的自在之物)以客观真实的反应客观世界。
所谓先验直观指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所有感觉都是人类为了实现依存对外部世界的扭曲感知:如视觉只在极有限的照度内对400~700 毫微米之间的光波可感;颜色不过是波长的光波作用于视觉系统的感觉转换产物;听觉不过是16~20000 赫兹的机械振动波刺激听器官所引起的“错觉”;触觉摸索出来的世界照例不过是形状、体积、温度和硬度等有所差异的武断的“感觉要素的集合”(马赫语)等等(具体可见《物演通论》第六十五章),人类用这种变换了物态的感官和感觉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生存所需的识辨系统,而且对于所有的动物来说,只有这种扭曲了真实的感觉才能最经济、最和谐地维系生命微弱的存在。
所谓先验综合判断指,同人的感性有先验规定性一样,人的知性和理性也有先验规定性,也就是说,人整理经验的手段也是按先天规定进行的,换句话说,无论感性、知性、理性,人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所有方式即感应方式都是有先天规定性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和理解,不同的文字之间可以翻译的原因——因为人类共同的逻辑形式(包括感性逻辑、知性逻辑、理性逻辑)是一样的。

何为身?身即结构。我们都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作为同一物类其生理结构或构造是一致的。虽然每个人的基因组型都是不同的(除非单卵双胞胎)即任何人都独一无二,世界上连两片相同的树叶都没有更何况人,但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生理性状上的局部差别,整体上每个人天生的能力总和是相仿的,即人的智商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但每个人的能力倾向是不同的,比如感性思维能力强的人适合从事艺术和技术,理性思维能力强的人适合数学和哲学。这种整体上相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生理结构,存在即结构存在(在《物演通论》中由存在度决定),万物即结构,从基本粒子、原子、分子、有机分子、生物大分子、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到人和人类社会都不过是一个个系统结构。
何为心?心即我们通常说的意识或精神或灵魂。其实我们的心首先是由我们肉身结构决定的感知方式,如低级神经中枢的发展使人类有了知性判断的能力,高级神经中枢的发展使人类具备理性抽象的思维。人的感应方式先天一致,但因为出身不同、环境不同、经历不同、教育不同,孩子在成长中形成的对于这个世界包括自我的认知也不同,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最初是外界占主导作用,但是,当一个人形成一个完整的稳定的世界观后,内在的认知就占主导地位了。如果不继续学习,可能就进入一种认知遮蔽状态而不自知,而不断学习可能就不断建构更宏阔更完整的世界观。
《物演通论》第一百零一章指出:
人类的精神文明就是从对“灵魂”的关怀开始的(所谓“灵魂”即是“虚体代偿主导实体存在”的初步自觉),所以才有了古埃及的木乃伊、金字塔、以及自发于各种族中的寄托灵魂的天堂、地狱和宗教思想。
也就是说,所谓“灵魂”就是感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对自我认知的自觉。而“自我”用黑格尔的话就是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并就此开始摆脱蒙昧,把人和自然界剖判开来,此为文明的开端。其实自我意识的确立只是人类更加弱化更加失位状态下的代偿举措,以便于定位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更好的求存。从“灵魂”或“自我”的发生学角度来看,人的灵魂或精神,包括自我意识,只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比如,电子通过它的负电荷能感应质子,质子通过它的正电荷也能感应电子,两者达成的结构叫氢原子;这种感应能力早在宇宙诞生伊始、能量开始转化为质量的时候就出现了。再往后,原子分化为分子,分子的感应能力远远大于原子;分子分化为细胞,细胞可以通过各种受体对各种粒子进行感知,其感应能力远远大于分子;再后来,细胞分化一步步导致具备视觉的扁形动物出现感性;生物进化(进化即分化)导致具备五官的脊椎动物出现了知性;最后具备高级神经中枢的灵长目动物出现了理性。在物质流变的过程中,感应逐步膨胀为感知,理性的出现才能代偿出“灵魂”或“自我”。
所谓主体的虚体代偿(感知属性代偿)主导实体代偿(实体结构代偿)指人类可以通过智质生产工具重塑自身,如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长,刨床和龙门吊是手臂的延长,汽车和轮船是足力的延长,电子计算机是脑力的延长。
存在度高的物质是没有所谓“灵魂”与“自我”,“自我”是存在度低的主体在失位状态下寻求定位的精神代偿,失位越严重,主体越残化,“自我”意识越强。精神代偿遵循简约原理(或思维经济原则),无论你感知(这里的“感知”包含感性、知性、理性在内的所有精神活动)多复杂,最后都会简约成一个“自我”的精神存在去达成和这个世界的依存。归根到底,“自我”就是自我认知。人从有了“自我”开始,就进入了文明化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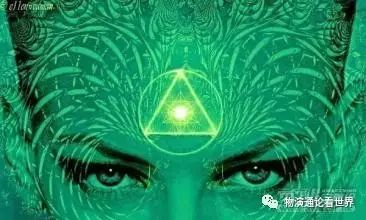
何为灵?灵就是心能达到的最高层级,即感性、知性、理性层级中,理性能达到的最高部分,以及这部分理性认知沉淀为知性本能的产物。
《物演通论》第九十九章在解读“理性逻辑”时指出:
理性思维一旦得出某种结论即成其为“知”,也交付于“知”。这意思是说,既然知性是介乎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层面,则它自然就有两个来源或双向延展性,一方面是直观的潜意识(或下意识)的知,一方面是推理的显意识(或明意识)的知,然显意识的知一经确定为“知”,即从推理中摆脱出来,或者说也随之沉淀为某种潜意识,这就是上中枢与下中枢的生理性逆向转递机制。这表明“知”必有一系列完全契合的贯通原则,也表明“知”必有某种发生着位移的基本准则。
也就是说,我们自认为本能或潜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东西,一方面是先天的认知基底,一方面是后天的理性沉淀结果。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是拿出生的婴儿比喻理性最清明的状态。但二者还是不同的,我们会说老子、庄子是得道之人或佛陀是觉悟之人,但没有人会认为婴儿是得道觉悟的人。老子作为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遍览群书、庄子用司马迁的话说“其学无所不窥”、佛陀更是接受了帝王家最好的教育几乎学尽当时所有知识,这样拥有的认知才是一个完整的不割裂的世界。所谓得道所谓觉悟,归根到底就是认知。先天沉淀在我们无意识基底的世界的统一性设定,必须要经过理性的追本溯源,把繁杂的“多”的认知还原为简一的“一”的认知,才算是通彻天地的觉悟。这种觉悟一旦在显意识中得到确认,就会沉淀为潜意识,这时便有了神秘感。佛家所谓证空,道家所谓见独,都由此而生。没有最高理性的完整认知,就没有深层直觉或灵性上与理性的逻辑融洽。否则,每个婴儿都天然的处于证空见独的境界,这肯定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而人类认知的发展过程是个分化过程,从前神学、神学、哲学到科学,当今没有人可以学完所有知识,甚至单单某一专业细分下去,你都不可能全部学完,于是,人的分科分工导致个人认知越来越狭隘,正如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哲学追求终极的功能就是透过这些破碎的知识表象,找到知识的分化路径,明晰各专业的本质,打破专业之间的边界,把纷繁杂乱的知识耦合成一个完整简洁的认知世界。如王东岳先生的《物演通论》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文明化程度到哪个地步(即人类衍存到哪个位相),知识的分化就到什么程度,人类文明越发展,要把越来越分化的“多”整顿归一就最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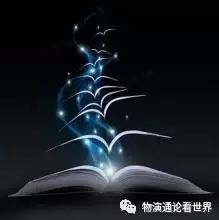
故,身心灵的修行,最关键就是认知,认知到什么境界,行为就跟着到什么程度。在“多”的层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术无道,如管中窥豹;在“一”的层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道术不孤,能看明白世界和人性。
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治心。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可用佛家比喻的人生三境界即是第一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当我们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时候,是因为我们眼中只有山和水,而山水只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日常经验中的人和事物。这时候,我们看不到山水的本质,不明白山水之所以成为山水的缘由以及它与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更不知道它以后的归宿;就好比你不知道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你为什么成为你,你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关系,等等。这时候,你以一颗单纯的本心看世界。
当我们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时候,我们的认知提高了,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时候每个人因着认知的水平不同,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只有能完整理解这个世界,把握住世界的本质(即老子的得道、庄子的见独、佛陀的觉悟等)的人,才能彻底理解整体下的局部,知道万事万物包括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自己是谁,此山此水此人为什么如是呈现等等。这种人如果是在他所处的时代缔造了新的世界观,我们称之为思想家,如前神学时代的老子与孔子等;神学时代的释迦、耶稣与穆罕默德等;哲学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与康德等;以及科学时代的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与爱因斯坦等。每个思想家都是站在前思想家的肩头攀爬到更高的思想巅峰。如果你理解了思想家的世界,就懂了人类思想的发展和样貌;如果你懂了当下思想家的思想,你就拥有了当下最开阔的视角和最强大的整顿当下信息、理解万物本质的武器和能力。就如同王东岳先生站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肩头,用“递弱代偿”原理缔造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世界,通解自然、精神、社会即万事万物,让人类自己更清楚世界的本质规定性及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时候,我们的认知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成为觉悟的人,成为所谓“神”。不为别的,就因为认知层面的极致提升,让我们不再以个人的视角而能以整个存在的最宏阔的视角审视人类和自身。
《孔子家语·好生》中记载:
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其义为:一次楚王出游,把他的弓遗失了,左右的随从请命去找回来。楚王说“”不用了,楚王失去的弓也是楚人得到,为什么要找回来呢?”孔子听了之后说,可惜楚王的思境不大,没有说不过是有人遗失弓,有人得到弓而已。为什么一定要是楚人?
老子听了之后说:为什么一定要是人呢?得弓失弓而已。
也就是说,孔子的思境消弭了楚人与人的差异,老子的思境消弭了人与动物的差异。哪怕人失去的弓猴子得到了,弓还是弓,得失只是从当事人(或动物)的角度而论。就如同一个人为自己的国家开疆拓土是英雄,但在被吞并的小国国人眼中无异是强盗是侵略者。所以,若以人类为整体的视角而言,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切战争的根源。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不过是被国家的意识形态洗脑后维护国家利益的集体主义的牺牲品。若以人类为整体的视角而言,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东西。正如王东岳先生《人类的没落》中所言:
时至今日,王尔德的一句名言已成为人类命运的咒语:“爱国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美德”。因为,“国家”历来是人类抱团攫利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人类之自私、贪婪、残暴和愚蠢等劣根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或者换一个更概括的说法,是截至目前的一切晚级社会之病害和文明人间之罪戾的温床与载体。此外,它还是人类集团化竞争的制高点,就像高考是中小学应试教育制度的关键点一样,故而可以再加一句评语:国家乃万恶之首。(此说的侧重点在于外向,即在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或国际纷争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恶性牵制;但并不排斥马克思式的内向批判,即国家对内也是阶级压迫的罪恶工具和人际纷争的浊臭舞台。)
也就是说,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大相径庭的结论,浅层视角的是非、对错、生死、大小等都是相对的,都可以在更大的视角下得以消弭,即庄子的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等。
而以最大最终极的视角关注万物、人类和自身,所做的、该做的仅仅是更好的活着而已。(这个结论的推导需要阅读王东岳的哲学著作《物演通论》)而如何才能更好的活着,非得有整体视角的大智慧才行。这个智慧就是最深刻的理性沉淀为我们知道该怎么活的本能后的“灵”。
就人类而言,所谓灵,就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世界观,就是能维护人类续存所需要的最恰当的文化。肉身代代被抛弃,存留的只有基因和文化,构成人类身心的延续。文化作为智质传承所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大于肉身基因的传承。

如果我们走过了前两个境界,最后就会返璞归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时的返璞归真,是理性智慧沉淀为本能后的化繁为简的智慧,也就是前述的灵性和觉悟。也就是说,天然的孩童的纯净和历尽红尘修行而悟的纯净还是不一样的,一个简单 ,一个丰富,前者自得,后者自觉,前者自然,后者是返璞归真的大智慧。孩子是单纯的天使 ,大智慧者是成熟的天使。
一个人,就算你彻悟了天地大道、拥有了最广宽的思境,如庄子与天地精神往来,或者说明白了世界的“本原”,可是,谁的肉身能活在“本原”的境界中呢?庄子不做漆园吏后还得卖草鞋为生,哲学家若没有积蓄不为稻粱谋则容易饿毙,曹雪芹作为最伟大的文学家却连家人的生计都无法维系。所以,无人能真正脱离红尘,庄子仍然“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苏东坡“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而也正是在“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现实红尘中,才能以出世之心,观红尘之事,在离不得的红尘牵挂中继续修行。
已识乾坤大,更怜草木青。所以,佛陀在觉得彻悟了天地而再无意义的时候,因着婆罗门教大师的建议有了新的发心去布道;王东岳先生在彻悟了天地而再无意义的时候,因着自身学问对人类求存的重要性而把讲学当做修行,并且不断俯下身去,绞尽脑汁试图用更大众更简洁而通俗的表述说明深奥的哲学及最重要的事关人类如何自处的递弱代偿理论。
路漫漫其修远兮,人生始终在修行的路上,因为人始终是人不是神,也没有必要用所谓“神”的标准要求自己。跟着自己的认知境界做人做事最自然。修行并非因理性而无情,而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王阳明先生和一位有道高僧交谈,忽然问大师:“令堂尚在否?”“在”“想她吗?”高僧羞愧的低下了头。先生说:“念自己的母亲,是人之本性,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啊!”第二天,高僧还俗了。
庄子说:“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也;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可逃于天地之间也。”
情与义,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比理性更深层的求存代偿。有多少人,辛苦辗转努力挣钱,只为家人孩子能生活的更好;有哪些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放弃身家性命,只为国家民族更好;还有谁,牵挂的是人类的未来,书以载道,言以传道,殷殷希望的,只是人类前行的路可以走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