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演通论看世界之二十六:释《道德经》第一章
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所以,任何理论都是对这个世界的解读,正确的解读必然殊途同归,即使语言不同,概念不通,所以佛陀说佛法是树上叶、语言是掌上叶,说理论或语言是指月的手指,而不是月亮本身,故,真正读懂经典,是见所有经典之同;但任何经典都是对当时信息量的归纳总结,不同时代不同的信息量下的经典,又必有其异,故见同而知异,才是对不同时代经典所蕴含思想的真正理解,也才能真正理解人类思想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走过的路径。
《物演通论》的作者王东岳先生常自诩为当代老子,因为他基于当下自然科学的最大信息量耦合整顿出一个全新的宇宙观模型或世界观图景,这个“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模型是老子宇宙观模型的升级版和精致版,且是一个证明体系,所以,也可以说有着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世人读《道德经》已不易,殊不知读《物演通论》更难,所以,我希望借着“物演通论释《道德经》”,让大家能更快更好的了解这两部经典。
需要说明的是,在《道德经》传承和发展的流传过程中,有众多版本,如楚简版、帛书版、河上公版、王弼版,而王弼版是流传较广的通行版,所以,我选用根据王弼版自己整理后的八十一章逐章解读,因为《道德经》的成型本就是一个在流传中不断被修订的创作过程,王弼版后的各版本之间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基本一致,各版本纵有细节出入,也不会导致悖逆原文的后果。另外,正如《物演通论》是个整体,三卷内容彼此融合,《道德经》也是个整体,故解读中常常根据前后章节的一致性来互解,即以经解经,以避免主观臆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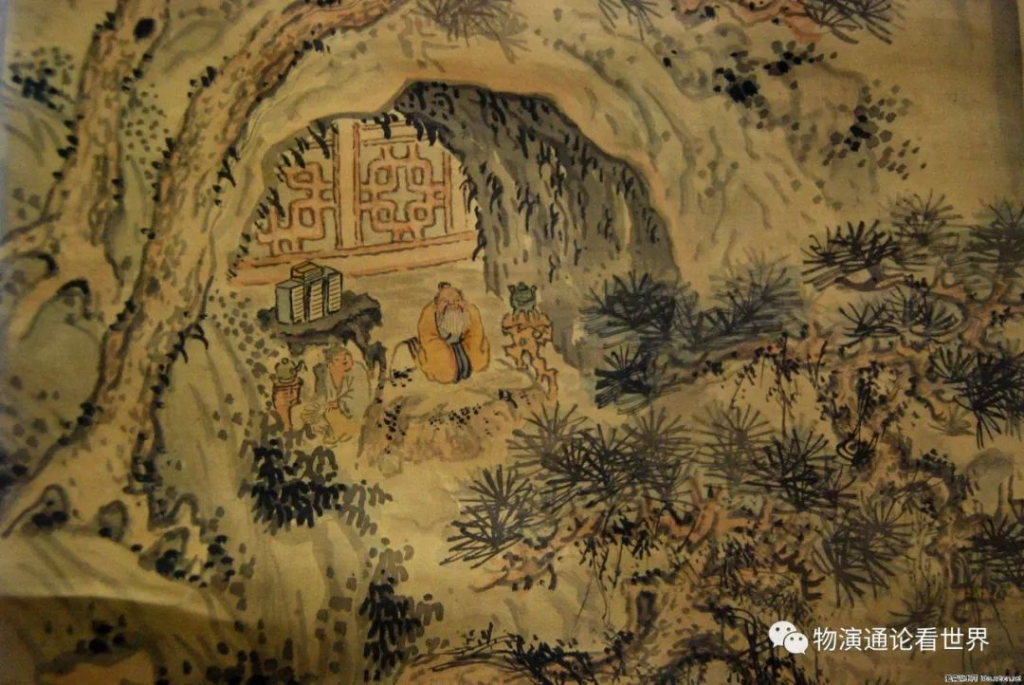
《道德经》第一章
原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首先我们额外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这样断句。
须知,第一章还有其他断法,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虽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点黑格尔的从肯定到否定,再肯定、否定的发展观,但遍览后续章节,虽然有“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的辩证说法,但没有明确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反而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的从一到多、由简而繁的分化发展,且二十五章中“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十四章“绳绳兮不可名”来说明运用形而下语言表达形而上思想的勉强,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更贴近作者想表达一种形而上的天之道而不得不用形而下的“道”来表述,“强为之名”、“不可名而名”来表述的不得已。
至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断法更是可以从后面的32、34、37、41、57章这些与“无名”“有名”“无欲”相关的章节得到确证:
32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始制有名”
34章:“大道泛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
37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
41章:“道隐无名”
57章:“我无欲而民自朴”
而且,在“名”之后接着谈“无名”“有名”,“无名”“有名”之后承接“无欲”“有欲”(从物之名到人之欲)很自然;从“名”突然到“无”“有”、“常无”“常有”不自然。虽然四十章有“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的关于“有”和“无”的单独用法,但若以“常无”“常有”解,去掉“欲”字更合理。且帛书版本“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就可以直接否定“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断法。
当然,《道德经》出现多种断句方法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版本的流传发展使其不是一个人完整思想的严谨表达,不具备严密的逻辑连贯性。有众说纷纭的理解和断句就再正常不过了。我们不过是尽力去找到它前后的逻辑连贯,并把它梳理解读为一个更好的逻辑模型。
断句问题解决了,其意思自然就明确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以“道”比喻形而上的存在本原(古希腊本体论质料因上的物质可分的最小单位)或运行规律(古希腊本体论形式因上不变的理念)。“道”当时的形而下含义是指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大道,即武王克商后,在西周所建的打通两个首都丰镐和洛邑的康庄大道。老子以此道比喻形而上的“道”,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而“名”指属性,我们能感受到的物质都是物质的属性,所以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第一章)、“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等都是表示无属性的质量存在之前的奇点能量态存在,当然,当时没有现代宇宙论的奇点说,所以老子称其为“道”,称其为“无”。杨朱讲“名非实,实非名,名无实,实无名”,也是指“名”跟“实”是两回事,因为“名”只是流变的属性存在,而不是不变的本性存在或存在本原。所以,“名可名,非常名”指根据物质属性所做的命名并非对物质的本质表达,而只是那个本质的语言载体,正如释迦牟尼所说“我所知法如树上叶,我所讲法如掌上叶”,语言只是指月的手指,而不是月亮本身,语言的局限永远不足以表达那个物质或事物的本质内涵,尤其是形而上的内涵。莱布尼茨也指出哲学需要专门的语言符号。黑格尔同样表示“我一旦用文字来表述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就已经失真了。”故,任何命名或语言表达正如《物演通论》一百六十一章中所言“语言符号必然暗含两项武断:即语言在表意或概念上的武断;以及语言被他人或众人承认和接受上的武断”。
具体到《物演通论》的理论模型上,“道”就如同作为始基存在的未分化前的奇点能量态存在(即四十章“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的那个“无”)和作为物质演化规律的递弱代偿法则(即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存在第一因)。“名”自然就是作为整个物演之流彰显的属性存在,各个学科都基于不同的理论体系用不同的概念和语言表述着这个属性存在,表达着同一个世界。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基于“名”的正确理解就毫无困难了:无属性的能量态存在并非真的“无”,它孕育出(在《物演通论》的模型下即分化出)质量态的有,而对质量态的万物予以命名,也就是能够在语言上表述了,才证明了万物的存在。正如哲学上的语言论转向所彰显的那样:语言破碎处,万物不复存。也就是说,当人类进化到用语言来建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时,语言上不能表述的存在,无法被其他人接受和认知,等于不存在;正如将来人类全面步入大数据时代以后,没有进入网络被数据化的,就等于不存在。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句话中,需要明白的是,虽然省略了主语,但“观”的主体显而易见是人。而“观”有两种“观”法,一种是“无欲之观”,能观其妙;一种是“有欲之观”,能观其徼。
所谓“无欲之观”就是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混而为一”的“整体观”,才能“观”得“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的察古知今之妙;就是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之“观”,才能“观”得“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追求终极之妙;就是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不出户、不窥牖”却见天道奥妙之“观”(即庄子的“朝彻见独”之“观”,所谓“见独”就是“见一、见整体”)。归根到底,就是打破所有边界的整体观。正如王东岳先生打破所有分科界限,耦合所有分科知识,才能“见”整个宇宙的递弱代偿原理之妙。也就是说,“无欲之观”求的是思想,而不是具体的知识,所以才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无论如何博学,如果不能把所有知识一以贯之,就没有得“道”;唯有达成“简一律”的“为道日损”,才算得“道”。
须知,简约原理是万物遵循的基本原理,在逻辑上表现为思维经济原则(或奥卡姆剃刀原则),理性逻辑的最高成就就是把繁杂的现象归结为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如牛顿的整个力学系统可以表达为一个方程式F=ma;爱因斯坦的基本思想可以用E=mc2予以阐明;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巨著及其全部进化论学说可以归结为“自然选择”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而《物演通论》表述的宇宙演化规律归根结底也就是一条“递弱代偿原理”。(理性逻辑的四条定律见《物演通论》第99章)虽然老子不懂逻辑学,但正如《物演通论》序言中所说:
几乎像是发自某种本能,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家都不自觉地──或者说是在尚没有什么根据的情况下──企图为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寻找根据。
因为,这是“先验的沉淀在意识深层中的一个无意识基底”(《物演通论》第一章语)。须知,逻辑发生的源头就是那个尚未分化的作为均质的无差别的“在”(或始基存在)的源头。分化后的万物凭借各自的感知属性企图回归为分化前的“一”,虽回归不得,但那种世界的统一性的根由却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在理化感应阶段,还是感性、知性、理性阶段一律表达。在理化感应阶段表达为感应一体;在感性阶段表达为对象为囫囵的直观的“一”;在知性阶段表达为同一律,即辨析表象下的“一”;在理性阶段则表达为简一律,即模型表象下的“一”。也就是说,物质演化的进程同步是逻辑演化的进程,顺序衍生出的无机物到有机物,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其感应属性增益或感知能力增强(即逻辑拓展),使其这种“一”由感应之点,扩展到感性之面,再到知性、理性之立体。故,简约原理下,感应属性增益到理性阶段的人类本能觉得世界是统一的,故,老子以“道”来统一,西方古希腊本体论阶段的哲学家泰勒斯则以“水”来统一,而阿那克西曼德以“无定形”来统一,还有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恩培多克勒的“火、水、土、气”,直到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另外一路,毕达哥拉斯则以“数论”来统一、欧几里得用“形论”统一、柏拉图以“理念”统一。(这段对于未学过《物演通论》的人而言如果太难请置之不理)
换句话说,“无欲之观”就是追求抽象存在整体之规律的学问,就是追求终极的哲学,在《道德经》中,就是以“天下”“世界” 这个最大的整体为对象,追求“一”或“道”, 即追求终极本质。
所谓“有欲之观”,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前提是先要有可“损”,即可“抽象”、可整顿的信息量。所有我们视为得道的人,无论老子、庄子、释迦摩尼,无不是学养丰厚。老子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近水楼台遍览群书,庄子用司马迁的话说“其学无所不窥”,佛陀也几乎学尽当时所有知识。而所有一点一滴知识的积累,从婴幼儿睁眼开始感性的认知世界,到学习书中的理论知识,每一步都是需要有清晰边界的。如果视觉混沌一片,我们不能区分任何颜色、形状;如果声音混沌一片,我们不能听到任何声音;任何概念没有边界的划分就无法成立;任何具体的理论体系没有边界就难以建立。所以,“有欲之观”,能观其徼。换句话说,“有欲之观”是具体的学问,是分科之学,相对于追求终极的哲学,是现象之学。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指“无欲之观”和“有欲之观”是相对的。当我们把什么视为对象时,什么就是整体。哲学把存在视为对象,存在就是整体。但如果我们划清边界,把某类存在物视为整体时,如把花作为研究对象,便有花道;把茶视为研究对象,便有茶道;虾有虾道,蛇有蛇道,万物皆有道,只是道亦分大小。只是,当老子以人为对象要追究“人之道”时,先要追求“天之道”,因为“天之道”是最大的道,作为最大整体的大道决定整体内部的局部的小道,小道只是相对的本质,相对于终极大道就成了现象,故,小道是大道的内容且服从大道。也就是说,大道和小道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小道是大道的现象,大道是小道的更深层的本质,所以说“无欲之观”和“有欲之观”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因为现象和本质归根到底是一回事(《物演通论》八十八章有详细解读),因为本质就是现象经过逻辑整顿后的结果。现象所涵容的信息量决定了逻辑整顿后本质能达到的极限,所以,在老子所处的小信息量的时代,无论老子如何博学,都整顿不出递弱代偿的逻辑模型,而只能端出一个相对粗糙的“天人合一”的逻辑模型,而且无力证明。
特别说明一下,“有欲”、“无欲”与“有”、“无”一样都是辩证表述,实际上不能清晰表达“玄之又玄”的追本溯源的追求终极之妙的过程。包括后续第二章、第二十二章等诸多章节都有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小信息量下思维的局限性造成了,同时代的西方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也都是这种辩证思维。如果换成非辩证法的表述,就会清晰的多,如二十八章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可以概括成“知其有,守其无”、“知其强,守其弱(弱能胜强)”,换成递弱代偿模型下的概念就是“知其代偿度,守其存在度”,而代偿度、存在度都是有矢量的,显然,后者的表意在明确其概念的前提下会更有效。同样,用分化前的始基存在代替“无”,用分化后的结构存在代替“有”,是更好的表达,且结构的复杂程度正是存在度的指标,也是有矢量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大学》中的话说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终极本质为本,则其他整体中的内容作为现象皆为末,由末而本即从现象到本质,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就好比植物学家探寻植物之妙,生物学家探寻生物之妙,打破植物与动物的边界,可探寻生命之妙,而继续打破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可探寻万物之妙,递弱代偿的物演规律就是打破层层学科边界,而找到万物一系的统一性原理。而一层层从相对本质到终极本质的探寻,就是“玄之又玄”的过程,最终找到“众妙之门”(即达成“简一律”的基本原理和终极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