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追问:何须惊异
哲学上所谓的“存在”仅指感知中的对象之总和。(1)
【一般认为,存在或在是对存在者或在者的观念抽象,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从根源上讲,不是在者集合成了在,而是在分化出了在者。对象未必是个别的,最原始的对象对于原始主体而言,一定是均质的,无差别的,亦即直接就呈现为在,而不是呈现为分化形态的在者。观念中的在,不是通过对众多在者加以艰深的抽象才在,而是先验的沉淀在意识深层中的一个无意识基底。所以,一般的主体通常不会对普遍的在发生惊异,反倒时常对个别的在者发生惊异。海德格尔说,从在者中引申不出在,是说对了的,但由于他不明白从在如何引申出在者,结果导致他的“此在”及其“澄明的临场”都不免陷入了无来由的黑暗背景中。】(2)
由于“感知”为何物尚属疑窦,故而对象以及对象的总和是否等同于存在物和自然存在则亦属疑窦。换言之,一旦对存在设问,那“存在”已是设问者感知中的主观存在了。(3)
所以,既往的哲学在通义上一概被囊括于形而上学之中,实不为误。也所以,概括说来,把感知中的存在作为对象的总和来研究乃为自然哲学,而把感知中的存在作为感知的总和来反思乃为逻辑学。尽管两门学问全然不同,但所究诘的却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方面。(4)
有鉴于此,立刻去分辨存在究竟是在主观之内还是在主观之外已无意义,因为分辨后的存在与未加分辨的存在并无任何异样或不同,反正无论如何你只能面对这样一种存在。(5)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分辨事宜暂且也着实无从下手。(6)
令人诧异的倒是,存在就存在着,何必多此一问。显然,这里有一个不得不问的缘由。(7)
也就是说,在对“存在”发生哲学性的惊异和探问之前,先有一个何须惊异以及何须设问的问题存在。【亚里士多德曾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引自《形而上学》)可也正因一切都起于这惊异,才使惊异本身不再被惊异。】(8)
故,哲学上的第一设问或设问前的潜在疑问应该是:作为存在者的设问者何以要追问存在?(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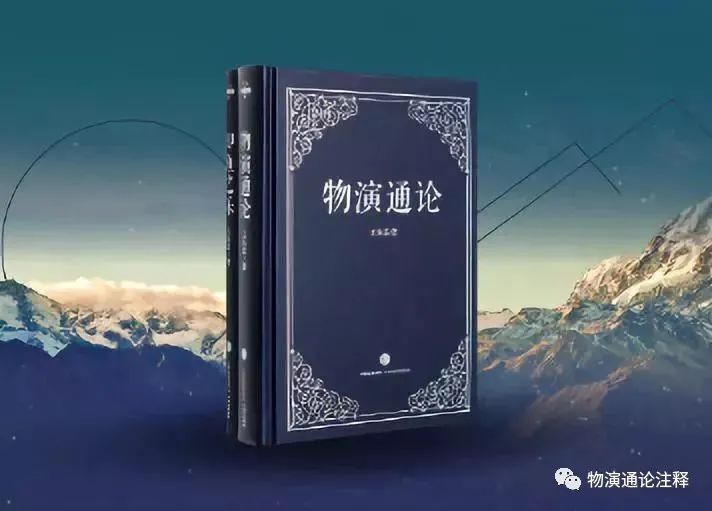
注释:
(1)全书第一句话作为对存在的定义言简而义深,读者对全书理解到什么程度,对这句话就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初读者和精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程度会差别很大。
简单的说,哲学追问“存在”都是默认以人为主体的,即哲学所说的“存在”是指人所能感知(包括感性、知性和理性,见卷二)到的所有对象或万物的总和。对其他物种而言的整个世界或“存在”是其他物种能感知到的对象或万物的总和:如蝙蝠的世界就是其超声波能感知到的一切外物的总和,狗的世界就是狗能感知到的一切外物的总和。(关于“对象”和“感知”的概念,卷二都有更深入的解读)。也就是说,面对同一个世界,不同的主体感知到的世界是不同的:非同类的动物之间如人和蝙蝠的世界图景完全不同,就算同类的人,因为兴趣的不同、专业的不同,对这个世界的信息摄取自然也不同,建构的世界图景自然也不同。只不过,《物演通论》不在个体上讨论问题,而是在人类整体上讨论问题。
作为人这个物种,忽略掉个体基因下的细微差异,其感知方式是相同的:因为感性逻辑(即眼耳鼻舌身的先验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觉能力)相同,所以我们看到的同一个物体基本是同样的模样;因为知性逻辑(即本能的判断,与感觉同步完成)相同,我们都会趋利避害,在同样的危机中本能的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理性逻辑(即狭义逻辑)相同,各个国家的语言才是可以翻译的。本书谈到某存在者时,都是以物种为对象,所以没有个体感知所得和人类整体感知所得的区分,而能够成为人类共识的知识如自然科学、哲学,也必然是能契合人类之共同感知的。
这里的“感知”在作者讲大课《存在论的意义》时为照顾读者被简化处理成“感”和“知”:“感”是感性经验或感觉,是眼耳鼻舌身意对信息的处理结果;“知”是“感”后面的、对经验层层归纳、演绎后的纯逻辑的理性认知。理性认知的极致就是达成简一律下的宇宙观认知模型。所以,古希腊所追究的存在本体也属于“知”,只不过古希腊对于“知”的追究分为两路:“质料因”和“形式因”。其中“质料因”的追究导出了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再经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恩培多克勒的“火、水、土气”,直至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而达到成熟;“形式因”的追究以毕达哥拉斯的“数”为开端,经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过渡,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念”而达到成熟。欧几里得的“形论”是它的继续表达。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是它的最后总结。
而对“感知”更完整的细分包括了理化感应、感性、知性、理性,在卷二统称为广义逻辑。作者在讲大课《宇宙观的意义》时,则被更通俗的细分为无意识、潜意识、下意识、上意识和思想意识。但无论怎么划分,作为整体的“广义逻辑”和“感知”的内涵是一样的。
深入的说,这句话中蕴含着作者要表达的三重假象:
第一、在本体论阶段,巴门尼德最早提出“存在”的概念,把对本体的追究转化为对存在的追究,所以,本体论也称之为存在论。这时,巴门尼德意识到流变的万事万物都是现象,他相信还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性存在(即本体存在)主宰着万事万物的流变,这是当时他意识到的哲学的任务。换句话说,他明确了现象与本质的差异,把现象视为假象,把本质视为真存,但还没有意识到“感知”本身的规定性(即“感知”的非真性)。所以,巴门尼德追究的“存在”的前提是意识到了第一种假象,即作为现象的假象,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本体论阶段的假象或古希腊的假象,这在卷一的存在论模型中对应为代偿性存在之假象,而非本性、本真或本质之存在。
第二、当笛卡尔开始怀疑“感知”(简化为“思”)的真实性时,对“存在”的追究就迈入了认识论阶段。对“感知”规定性的追究意味着哲学家意识到了“感知”造就的第二重的假象,由此引发了康德对于感知规定性最深入的追求,奠定了近代“知识论”的基础,即说明“知”何以成为“知”,由此也把认识论转化为知识论,一如巴门尼德把本体论转化为存在论。认识论阶段对逻辑形式(即感知规定性)的追究意味着哲学家意识到了感知非真,所以,我们把这种感知非真造就的假象称为认识论阶段的假象或康德假象,这在卷二中扩展为对整个广义逻辑(包括理化感应、感性、知性、理性)的反思。所以,基于当下“存在”的内涵已经与古希腊巴门尼德的阶段完全不同,作者才会澄清性的指出“存在”概念的新内涵——哲学上所谓的“存在”仅指感知中的对象之总和——即一切“对象”都是感知造就的非真的对象,包括“对象之总和”的“总和”也是感知规定性下的逻辑整顿。所以,对卷二的“感知”理解到何种程度,直接决定了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程度。
第三、走过了本体论和认识论阶段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清醒的意识到“对象的总和”在人类不同的认识阶段其内涵完全不同:在低级认知阶段,只是感性经验的简单叠加;在中级认知阶段,会通过理性整顿出一个个逻辑模型;在高级认知阶段,哲学家会致力于把所有不同的逻辑模型整顿成表达了所有逻辑模型最底层逻辑的简一律下的新的逻辑模型。霍金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更是清楚表达了一切知识都是主观的逻辑模型。我们把这种逻辑模型的主观性确定为第三种假象,这在卷二的反思中表达为不同衍存阶段的存在者的感应属性代偿。所以,王东岳先生反复强调其缔造的递弱代偿存在度模型也是一个主观的逻辑模型,是人类社会在当下生存结构下的感应属性代偿,即暂时能达成逻辑三洽而正确的、暂时能满足人类代偿需要的代偿之“知”。换句话说,人类的任何知识都不是真理,最多只能达成暂时的正确,这种对人类知识的自觉不认真,因着霍金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我们也称之为霍金假象。换言之,古希腊追究的那个永恒的、不变的本质或本体是不存在的,这个本质是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说,就是这种本质的漂移。
由此可知,第一句话表达的“存在”的概念内涵远远比巴门尼德缔造的“存在”的概念内涵要丰富、深刻的多,但《物演通论》作为哲学书必须和西方哲学史包括西方哲学家用的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保持一致的关联,能沿用的概念就需要尽量沿用而不是生造词。所以,作者会在第一句对“存在”的定义前面加上“所谓”二字,意欲表达此“存在”概念与既往“存在”概念在内涵上的巨大区别。
具体而言,古希腊追究的存在本体是一个恒定的不变的存在。巴门尼德通过对“存在”和“非存在”的划分,把“存在”视为哲学追究的本体,不以认识为前提,即本书中提到的“元在”或“本在”,即康德称之为“自在之物”或“物自体”的东西,在古希腊哲人的认知中是永恒不变的;“非存在”是假象,以认识为前提,即被感知扭曲后的“对象”或“现象”,在古希腊哲人的认知中是始终流变的。而作者认为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本体”(或“本质”)与“现象”如影随形,同步衍动变化,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体的(详见第八十八章:本质是现象的逻辑整顿的结果)。所以,作为本质的存在和作为现象的存在都是流变的。
古希腊追究存在本体有两路:一路“质料因”,追究到原子、乃至现代更无限可分的基本粒子,而原子、基本粒子都不是肉眼可见的,只是科学家通过实验导出的逻辑模型,也就是通过我们的理性逻辑导出的认知成果;另一路“形式因”追究不变的逻辑形式,如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欧几里得的形论、柏拉图的理念,其实都是对主体先验逻辑形式的表达,如数学表达了先验的数理逻辑,形论表达了物质内部之间乃至物质之间的先验的广延属性关系(详见第一百零三章),理念表达了知性乃至理性的先验范畴关系。
也就是说,无论“质料因”还是“形式因”,虽然被亚里士多德错误的将前者视为原料或内容、将后者视为本质,但其实追究的都是先验的逻辑形式,而这个先验的逻辑形式在主体的演化进程中是变动的,如质子的逻辑形式是理化感应,扁形动物的逻辑形式只有感性,到了脊椎动物才有知性,及至人类才有完整的感性、知性、理性,但人类的智质继续分化(即分科),科学由此昌盛。故,这个逻辑形式是永远随着主体的衍存位相的变化而变化的,尤其在智人以后,智质分化加速,这个逻辑形式构建的逻辑模型高速变革,其速度远远大于世界本身的演化。
总之,要全面理解全书第一句对“存在”的定义,肯定需要理解卷二的“感知”(整个卷二都是解读作为广义逻辑的“感知”),更要理解“所谓”二字,这样才明白“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作为作者“感知中的对象的总和”,并没有把“存在”固定为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在固定衍存区间内从无属性的“在”分化衍动为有属性的全体的“相对存在”的流程。关于这一点可参考14章对“存在”的定义:“它不仅表象为一般外延上的所有具体存在者之总和,而且抽象为纵深内涵上的所有具体存在物之源流,而并不与存在物的感应状态或感知状态相关。唯因如此,它才得以从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性存在逐渐演成(或相对存在为)不可望而可及的理性存在”,只不过在这一句话,作者是站在存在整体的角度,把所有主体返还为客体,所以说存在“并不与存在物的感应状态或感知状态相关”。在卷二中,作者也是把主体返还在这个本体中,才说明了主体及其精神的由来,包括主体之“感知”中的存在与存在本体的预定和谐关系。(这部分解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读完卷二会慢慢明了。)
换句话说,在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下,巴门尼德追究的那个永恒的不变的本体真存是不存在,它本身一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化,在卷一作为“在”它被抽象为递弱代偿的存在性;卷二被还原为“知”成为继盖天说、地心说、日心说、牛顿的绝对时空说、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之后由递弱代偿存在论模型推出的时空物一体的超时空宇宙模型;在卷三它随着“知”引领的分化重塑知者(亦即在者),并通过人造物重塑自然,建构起最后衍的人类社会。
同时,在递弱代偿的存在论模型下,认识论阶段追究的感知规定性(即精神本体)也是随着世界的衍存分化而变化的,所以,精神存在并不玄奥,它从物理存在、化学存在的理化感应属性起步,一步步增益到扁形生物出现感性、脊椎动物出现知性、灵长类动物出现理性,最后到人类阶段发展到可以通过理性追究理性本身——即把“理性”当做对象予以反思,这时“精神”才得以成为独立的对象而存在。当然,能对理性进行反思时也必然能对感性进行反思,卷二就是对整个广义逻辑(包括了理化感应、感性、知性、理性)的最全面最深彻的反思。
我们甚至可以把全书都理解为对“存在”概念的解读,无论是卷一的“自然存在”、卷二的“精神存在”、卷三的“社会存在”,都既是借由作者表达的人类当下衍存阶段作为知者的“感知”之“知”,同时维护了人类作为在者的“存在”之“在”,因为“知”是“在”的感应属性代偿,“在”是“知”的载体或代偿结果,二者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存在。
所以,在卷一开篇第一章,作者并不去区分作为外物的自然存在和作为感知的精神存在,因为我们感知中的存在是外物和我们的感知形式(即广义逻辑形式)相互作用的耦合结果,它的存在同时证明了外物与我们自身的存在,换句话说,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不可分,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可分。于是,作者在卷一中建构存在论模型时就不再纠结感知本身的规定性,因为这本身就是自然赋予的规定性。
(2)因为第一句的内涵太过丰富,作者在第一章必须做一些必要的解释,于是有了第二段方括弧里的说明内容:
首先,我们的“感知”中既有对空间的横向感知,也有对时间的纵向感知,但既往哲学的“对象总和”都是横向空间下的“对象总和”,即其抽象处理方式是横向感知的观念抽象,所以抽象出的是西方横向思维下空间范围内的认知模型,如突显论、创世论都是这种认知模型,即世界是上帝在七天内创造的,是突然间展现为整个存在的。这是本体论哲学最后会自囿于形而上学的禁闭找不到出路,以致于滑向语言论转向乃至愈发肤浅的现代哲学的根本原因。所以,作者才说“一般认为,存在或在是对存在者或在者的观念抽象,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从根源上讲,不是在者集合成了在,而是在分化出了在者”。
“在分化出了在者”表达的是纵向时间感知模式下的抽象处理结果,也是全书与既往哲学全然不同的逻辑视角。这种视角造就的是演化论、进化论或分化论下的认知模型,即世界不是突然存在的,而是从无属性的存在分化为有属性且属性越来越丰富的存在,即“存在”是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分化进程。这是一种纵向思维下时间范畴内的认知模型。
在本书附录的《概念注释》中,作者对“存在”的定义如下:简称“在”,是对“存在者”(简称“在者”)的总体抽象,因而它一定是主观化了的存在,而不可能是客体的总和。
这里的“总体抽象”和本章第一句中的“感知”或“对象之总和”并无区别,都包含了对纵向范畴结构的梳理和抽象,而不仅仅是既往哲学家横向的对“在者”的观念抽象。也就是说,全书第二句“一般认为,存在或在是对存在者或在者的观念抽象”中的“观念抽象”没有包括作者特有的对于纵向范畴的抽象,所以作者与既往哲学家不同,把存在纵向的相对性作为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才有第三句“从根源上说,不是在者集合成了在,而是在分化出了在者”,这是作者特有的纵向抽象视角下的表达。所以,既往哲学家抽象出的只是逻辑形式横向观照下的逻辑规定性(如康德),而作者抽象出的是逻辑形式纵向衍动下的存在性(即递弱代偿原理)。关于范畴的概念学完卷二会更清晰,这里简单理解为万物纵向衍存中“类”的差异即可。关于横向空间与纵向时间的感知差异,要学到卷二九十一章才有更深入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对象未必是个别的,最原始的对象对于原始主体而言,一定是均质的,无差别的,亦即直接就呈现为在,而不是呈现为分化形态的在者。观念中的在,不是通过对众多在者加以艰深的抽象才在,而是先验的沉淀在意识深层中的一个无意识基底”,指的是:
人先天地觉得这个世界是统一的、有元因的,所以哲学家都试图追究这个世界的终极。但在纵向思维的时间范畴下,一定是先有抽象是均质、无差别的“在”,才有后续具象或具体的存在。显然,是我们视觉、听觉、触觉造就了具象或具体的存在,且不论视觉、听觉、触觉本身就是数亿年才能进化出的复杂的神经感知结果,包括我们自身都是更复杂的后衍性存在。所以,这个称之为“在”的终极并不是万物的横向抽象的结果,而是万物的纵向分化的源头,即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那个源头。未分化的那个“在”(或“道”)因为未分化,故均质无差别,即没有主客体,或主客体同一,即直接就是整个存在,而不是以有属性的在者的形态呈现。这个终极是我们能追究的这个世界的源头的终极,也是逻辑所及的终极。之所以说“观念中的在,不是通过对众多在者加以艰深的抽象才在,而是先验的沉淀在意识深层中的一个无意识基底”是因为意识是从无意识到潜意识到显意识一步步发展出来的,在人类还是“非人”的时候,意识(即理化感应)就在起作用了。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在”既是“在者”的分化源头,也是“在者”感应属性的分化源头(即逻辑分化源头),所以,它沉淀在我们潜意识乃至无意识的最深处,成为“让所有人先天的觉得这个世界是统一的、有元因的”的先天的逻辑规定性。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这个终极存在既是本体论物质的终极也是认识论逻辑的终极,二者本一体,它造就了我们,也造就我们的感知方式(即包括理化感应、感性、知性、理性在内的广义逻辑形式),同时也就造就了我们感知中的世界。
“一般的主体通常不会对普遍的在发生惊异”这里“普遍的在”指未分化的在(即《概念注释》中的“幽在”)或低分化的在,即作为本原性存在的抽象存在,即在衍存中逐步退为背景的那些后衍具体存在的低分化背景性存在(如时空)。人通常会对一个特殊的对象发生惊异,但不会对整个世界表示惊异。一般人只会问我为什么存在,而不会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存在。只有孩子会对所有存在感到好奇,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是哲学的基本素质。
理解最后一句需要明白,海德格尔的“此在”以“无规定的我”为讨论的起点,是“此在”的人本论;“澄明的临场”是指人的精神质态,在本书中是作为属性代偿的感知。关于“此在”与“澄明的临场”在本书二十七章、四十章也有提到,可配合理解。本书正是在递弱代偿的模型下说明了“此在”与“澄明的临场”的来由。
(3)因为我们说不清“感知”是怎么回事,故我们感知中的世界(即感知到的对象及其总和)是否等同于客观世界也是说不清的。也就是说,我们一旦追问存在,那存在已经是我们感知中的存在了,亦即已经是主观存在了。如同一只蜜蜂或者一只蝙蝠如果会追问存在(世界),那存在(世界)已经是它感知中的主观存在(世界)了,必然与人感知中的世界不同:如蜜蜂能看见紫外线,而人不能;蝙蝠通过超声回波感知世界,而人不能。同样,人感知中的世界,也是人特有感知方式下的主观世界。
(4)本段指:自然哲学和逻辑学探讨的是同一对象,即“感知中的存在”,这也是唯一可以探讨的对象,因为人类没有可以直达客观世界的另一套感知系统。把世间万物作为真实的存在或不去区分真实与否而去研究的是自然哲学,即以对象为本,以现象为本,探讨现象的规律;把世间万物作为虚幻的感知去反思是逻辑学或精神哲学,第八十八章明确指出:逻辑学也就是广义上的“主体性”或“主体感知属性”。整个卷二都是逻辑学或精神哲学的内容,即以感知为本反思感知,探讨感知的规律。实际上,自然哲学和逻辑学是同一物演进程不同角度的表达。自然哲学从对象作为实体结构的存在(第五十三章指出:“存在”表现为结构存在。其意指,实物都是结构的呈现)出发,从整体上探讨对象(包括人)的衍存规律。逻辑学从主体作为感应属性的存在(即存在都是主体的精神存在)出发,探讨精神的发生学原理和衍存规律。二者的关系在于:对象固然都是主体感知中的对象,但主体也是对象反客为主后的客体,即主体的本质是在纵向上与对象处于统一衍存系列中的客体。
实体结构代偿和虚体感应属性代偿,这是同一相对存在一体代偿的虚实两面:
注意这个“实”是结构代偿的“实”,在后面章节“万物一系”的表达中可知,其结构代偿之“实”,非存在本质即存在度之“实”,结构代偿之“实”只是存在本质最坚实即存在度最高的本原性始基存在的寄居“形式”(参考第五章:严格地讲,一切衍存者如原子、分子、生物乃至人类都不过是本原性始基存在如某种基本粒子或量子的寄居壳或临时寄存形式)。对于本原性始基存在,实体结构越复杂则越“虚”(即存在度锐减、感应属性的虚拟性增强),即古希腊哲学中与本体真存相对立的流变的假象;即佛家说的“虚”相——故《金刚经》曰:“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亦即叔本华说过的:“对一个人而言,假若他看见的众人和万物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幻想或幻影的话,他就不会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
而这个“虚”就是感应属性代偿,即感知中的存在皆精神存在。
更深一点来看,“感知”是包括感性(甚至理化感应)、知性、理性在内的广义逻辑。我们感知中的存在或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可感属性和人类感知属性耦合的结果。这种耦合绝不仅仅限于感性直观,比如我们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绝对时空到相对时空都是人类不同位相上用感知属性(这个阶段指包括感性、知性在内的理性)和客观世界耦合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把这些结果视为客观即存在本身时,这些结果是自然哲学;若我们把这些结果视为主观即认知本身去反思,便是逻辑学。显然,我们的认知结果(耦合结果)既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客体和主体二者共同决定的,所以说自然哲学和逻辑学虽然不同,“究诘的却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方面”——同一种东西就是我们感知中的世界或存在:表象的世界绝不仅仅包括感性的直观表象,也包括理性的模型表象。比如作者的递弱代偿理论就是一个模型表象,是作者感应属性与客观世界可感属性耦合(虚拟、抽象)的结果。当我们把这个理论作为对象的总和(即自然存在、即实体结构存在)时就是自然哲学,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当做感知的总和(即精神存在、即虚体感应存在)时就是逻辑学。
参看八十五章可知:“现象之知”恰恰是建立在“彼岸存在”这个“半壁”基础之上的;“本质之知”是进一步扩展到“此岸属性”之中的产物。也就是说,现象是联接主客体的唯一纽带,主、客体各占现象的半壁,所以说它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方面。只不过自然哲学取对象客观的一面,将其当做自然存在或实在加以研究;逻辑学取对象主观的一面,将其当做精神存在或虚体感应存在加以研究。佛家所说“心不自心,因物故心;物不自物,因心故物”也有点这个意思。
参看第一百七十九章,也明确指出自然史和逻辑史原属一脉,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或逻辑存在)本就是同一存在的不同视角,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或逻辑学)的研究也不过是同一存在的不同视角。
(5)感知中的存在是我们唯一面对的存在,无论视其为主观的精神存在还是客观的物质存在都无法证明(唯心不能证明自己的纯主观,因为不能说明感知或精神是什么;唯物不能证明自己的纯客观,因为不能说明物或对象是什么),所以无论区分与否、如何区分,外物和精神都是不可分的一体存在,不如暂时不去区分。总之,因为外物和精神不可分,则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可分,则自然哲学和逻辑学不可分。于是,自然哲学的追问只能就“感知中的对象”展开。
(6)哪怕你想分辨存在在主观之内还是主观之外,因为人的“分辨”方式即感知方式是先天的、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所以也无从下手。
(7)倒是万物的存在中为何只有人追问存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人不得不追问存在的原因是哲学上的第一设问。
(8)对这个世界的惊异是哲学家应具备的素质,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这里“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指的是对作为整体的万物的惊异,所以实际上是在追问存在,存在即具体的万物后面那个整体的抽象存在。
而追问存在之前有一个为什么要追问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何须惊异或何须设问的问题。这是从亚里士多德追问存在到追问亚里士多德的追问,故成为新的第一追问,表明了逻辑极点的前移。换句话说,既往的哲学只追问存在,于是不再追问为什么要追问存在。
(9)所以,新的第一追问是:作为存在者的设问者何以要追问存在?即亚里士多德作为存在者中的设问者为什么会惊异,或者说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追问存在。
(具体答案见第58章中:追问存在的存在者一定是由于自身的弱质而发问,或者说一定是由于自身需要代偿而发问,这就是作为“存在者”的“设问者”何以要追问存在的原因。
也就是说,追问是一种能力,无机物、低等生物都是比人类存在度更高的强存者,无需此能力即可生存;而人作为后衍存在,存在度降低,必然需要能力来弥补:这就是人追问存在的根本原因,即追问存在是人这个弱存者生存的需要。但这个结论的导出基于递弱代偿的本体论模型,在这个模型未建立以前,本章作为本体论的开篇需要找到新的本体论的逻辑极点,即“作为存在者的设问者何以要追问存在”。 )
注:在本章中作者提出哲学上的第一追问是“作为存在者的设问者何以要追问存在”,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惊异”(“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只是原来的逻辑极点,“为什么惊异”才是比“惊异”更前面的新的逻辑极点。
须知,其他动物都无需追问,只有人类必须在追问中生存,人类的文明就是在追问中建立起来的。明了“何以要追问”(即“为什么惊异”)的本质是自然哲学的第一问题。
关于本书每章中的涉及的重要概念,读者既需要参考具体章节中的论述,更需要参考概念注释中的论述,因为具体章节中的论述需要关联上下文,而概念注释中的论述往往立足于整体,有时候显得更完整、更全面。所以,每章的最后,会附上本章的重要概念,并汇总不同章节和概念注释中的定义。
附:本章重要概念:
一、存在
(第一章):哲学上所谓的“存在”仅指感知中的对象之总和。
(第十四章):“存在”——它不仅表象为一般外延上的所有具体存在者之总和,而且抽象为纵深内涵上的所有具体存在物之源流,而并不与存在物的感应状态或感知状态相关。唯因如此,它才得以从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性存在逐渐演成(或相对存在为)不可望而可及的理性存在。
(概念注释):简称“在”,是对“存在者”(简称“在者”)的总体抽象,因而它一定是主观化了的存在,而不可能是客体的总和。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
希望本公众号对您学习《物演通论》有帮助!思想的传播需要我的初心和坚持,也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励!欢迎提供反馈,或赞赏、转发,或批评、指正。谢谢!
1、欢迎读书困难的同学关注“物演通论注释”公众号,有逐章的注释以供参考,二维码如下:

2、请关注“物演通论看世界”公众号,二维码如下:

3、请关注“物演通论读书会”公众号,二维码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