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演通论看世界之六十七:从《奥本海默》说起 (非影评式观影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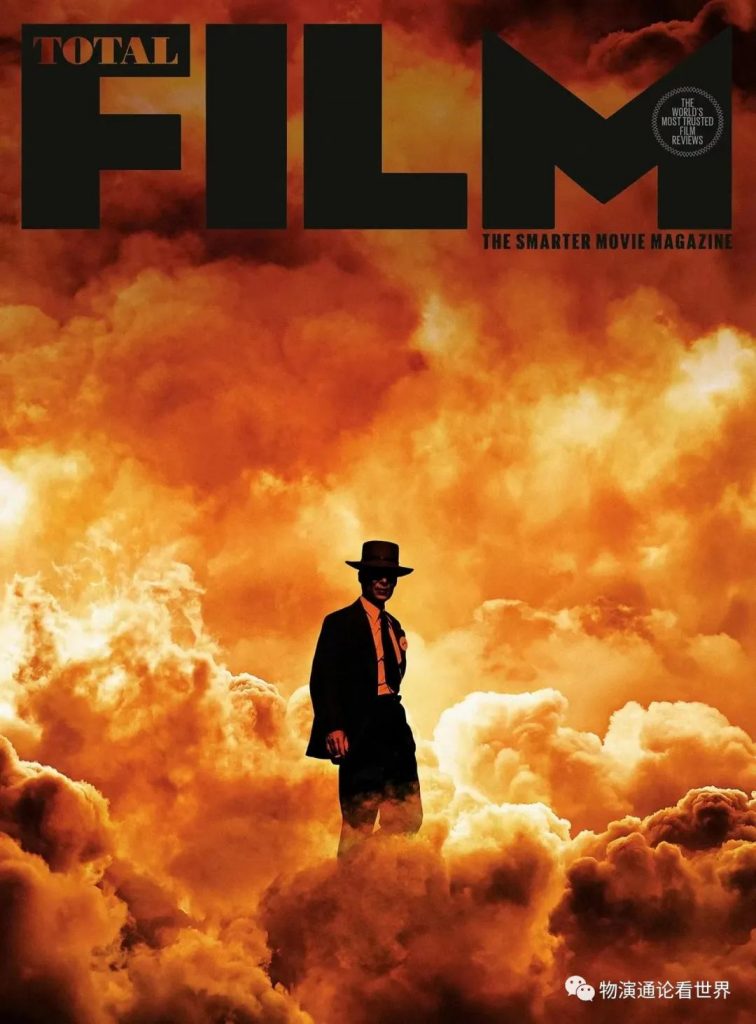
(一)反思是本片的最大价值
《奥本海默》的影评太多了,介绍科学史背景的,介绍剧情的,剖析导演创作手法和风格的,任何想了解这些的人,都可以按流量依次看这些网络上的影评,我不用再重复,也不喜重复。我唯一愿意不厌其烦重复的,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涉及的思想性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深度看世界、整体看世界的的关键。
我不是诺兰的影迷,看这部电影也不是因为诺兰,而是因为偶尔看到影评,知道这是一部表达奥本海默的反思之作。导演愿意拍,至少证明导演也是在反思的。在我看来,导演拍的任何影片从根本上表达的都是导演的思想,是导演在借影片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诺兰不懂《物演通论》,其反思肯定是有限的,但他也指出《奥本海默》对于现今展开的无限升级的AI是有提醒其反思的借鉴作用的。对于所有意识到AI危险却不肯放弃AI研究的科学家,当下就是他们的奥本海默时刻。但世事往往如此,只要危险没有展现在眼前,只要伤害没有成为事实,只要种内竞争还存在,谁都不会放弃科技乃至武器的升级,但导致的结局是需要人类共同承受的。不仅AI,生化武器、基因编辑都一样。学《物演通论》的人比任何人更懂得其绝对危害。
所以,虽然这部影片的反思没有哲学的深度,但反思,仍然是这部影片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当下,整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反思,不仅仅是对核武器的反思,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反思,而是对人类当下处境的反思,对当下主流文化的反思,尤其是对科学的反思……
人人都有成见,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断反思,才可能成长;人类也一样,必须意识到所有文化都只代表着一种成见,并通过文化反思,乃至思维方式的反思,甚至感知方式的反思,才可能认清人类自身的盲存状态,从而有望让自己稍微清醒那么一点点。虽然这种清醒可能让人觉得天地倒悬。
严格来说,任何文艺作品乃至艺术作品对思想的表达都是极其有限的,但却是受众最广的,任何思想大众化的最佳途径永远是受众最广的影视作品。所以,我这篇文章也算是蹭热度的,其目的不是帮助你看懂这个电影(这个其他影评足以胜任),而是想让你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电影,或者,希望您能稍微看懂这个世界多一些些。
人类一般都是出现了问题才会反思,如神学时代,人们以为是上帝庇护了它们,直到黑死病要摧毁人类,人们才开始怀疑上帝、质疑上帝,反思上帝存在与否。现在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已经如此之高,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已是如此强大,为什么人类反而危机四伏?!如经济危机的周期越来越短,全球性疫情的频率越来越快(如从非典到新冠,这里抛开了美国有意为之的阴谋论,而是单纯将其视为文明病的一种;但人类随时都可能承受类似疫情的生化战争),气候异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核战争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糟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是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标志)……人类是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糟了?以前再残暴的人,也不可能灭绝人类这个物种,如成吉思汗动不动就屠城,但人类这个物种无虞,但今天科技赋予人类的力量,无论是直接的各种武器(如生化武器、核武器、人工智能武器)还是间接的环境恶化,都足以灭掉人类这个物种,这充分表达了人类整体存亡的系统危机越来越显化。也正是有这方面模糊的感知,西方总是会拍些末世的科幻电影,但为什么可能导致末世,他们说不清,更没有因此而反思其文化,并做出任何改变,最多把导致环境恶化的工业生产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同时还能降低人力成本。
所以,也不能说西方完全没有反思,至少他们意识到了环境问题,如美国早就明白地球承载不起几十亿人的高消费。但针对这个问题,美国不是进一步反思高消费的文化,而是奉行美国至上的原则,以保证地球资源可以满足少数人的挥霍,大多数穷的国家必须永远穷,想稍微过好一点,也需要经过他们允许,即允许进入WTO,但富裕的程度超过他们的允许范围,随时有金融办法收割你。但霸权是不可能长久的,民主、自由、平等在国家之间都不存在,口头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就变得虚伪,只有还盲目崇拜旧秩序和主流文化的人群才极力维护着那一套把持着话语权的旧的说辞——当然,在目前的国内,信奉这一套旧说辞的占绝大多数。
全球化的趋势可能反复,但不可逆转,这就要求全球必须凝结成命运共同体,联合国必须肩负起维护人类整体求存的职责,人类才有可能在新的匹配全球化结构的新文化的濡染下,共同应对系统危机的问题,共同维护人类的整体求存。
(二)深层反思才能拯救人类
任何一部电影,因为每个人认知的不同、关注的角度不同,感受也肯定不一样。
电影一开篇就是普罗米修斯的神化故事,因为作者把奥本海默比作了普罗米修斯。但我内心直接联想到的却是王东岳老师的《知鱼之乐》中的一篇文章《普罗米修斯的天谴词》,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把人类最初的“火”,也就是把分子物质剧烈氧化释能的现象称之为“地火”,把原子聚变或重核裂变释能的现象称之为“天火”。也就是说,该电影反思的是“天火”,王东岳老师反思的不是单独的“天火”和“地火”,而是包括了从“地火”到“天火”的人类文明进程。当然,普罗米修斯的神化中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当然也是因为他盗了“地火”,这是因为在文明初始的那一个轴心时代,反文明的意绪在各地的文明发端皆有表达:如基督教的《圣经》面对无知无识直接向自然获取资源的采猎文明过渡到必须掌握更多知识并辛勤劳作方得温饱的农牧业文明喟叹为“失乐园”;如释迦摩尼代表的佛学讲“戒、定、慧”,就是通过抑制智质上的分化或发展来维系自身的相对圆满;如老子倡导“绝圣弃智”、“见素抱朴”,追求“小国寡民”就是从中原农业文明下的战乱频仍和周边原始氏族社会一片安宁的两相对比直观的就意识到了人类文明趋势不良,故声明“吾从商”;如老子的学生孔子也宣扬“吾从周”……这充分说明处在文明发端的智者不约而同的感受到了文明本来的狰狞面目,只不过后来的人们在越来越枝繁叶茂的文明大树下,一叶障目,尤其是哲学分化为科学以后,表达整体、追求终极的西方哲学越来越无所作为,丧失了追求终极的能力,以致于科学越来越看不清整棵大树了,于是面对着每一处新抽的新芽新叶欢呼雀跃,更是把科学时代称之为“群星闪耀”,只不过这星光照耀的是人类的灭归之路还是光明之路,完全取决于是终极评价还是情景评价。
当然,哪怕是基于终极评价,个体的选择也会不同,如科学家中肯定有不惜生命也要完成或捍卫学术成果的,如运动员中肯定有哪怕以损坏身体为代价也要追求世界冠军之荣光的,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他们绽放生命的方式,就是他们实现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方式,就是他们的信仰和真理。但这只是少数人的选择,普通人不追求也求不得那刹那的辉煌,只希望平平凡凡、安安稳稳的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人类整体的求存求的也就是一个寿终正寝、无疾而终,而不是刹那的科技爆炸伴随着人类毁灭的辉煌。
生命最本质的意义就是求存,求存最本质的内涵就是维系存续。以此为基础衍存出的后发意义,不过是智质分化下,个体站在自己分化角度渴望实现自我的个体偏角下的生命意义。所以,在智质分化程度低的传统文化中,追求的反而是“平常”、是“中庸”;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至誉无誉”,庄子更是在《逍遥游》中直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以,《菜根谭》强调“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如《中庸》脱胎于“执两用中”、不走极端的方法论,上升为宇宙论,把“中”视为“道”或“本”,主张顺道而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意思就是说:只要遵循道,天地万物包括人间都会各自有序、有条不紊、天下太平。可见,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始终是合乎道,是整体安稳,而不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哪怕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会加一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为能力与德行不匹配时,能力越高,给整体带来的伤害越大。但人类最高的科技往往都是诞生于战争,是用于人类自戕的,而后,才从军用转为民用。
《中庸》强调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即,只有真心对天下百姓的,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典范,才能树立治理天下的法则,掌握天地化育万物的深刻道理,(有这些就足够了)还需要什么依靠呢?但事实上,天下早就不是一家之天下了,哪怕这一家最有德;而且,单纯的以德治国,早就不合适了,现代也一样,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别人不择手段、你一味清高,恐怕早就被逐出竞争舞台,丧失角逐资格了。但你若希望建立命运共同体,就必须以身作则,真正奉行平等、自由、民主的原则去对待其他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消解了种内竞争的共同体。
竞争与协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永远交织的主旋律,竞争的主体也从氏族社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逐步上升到今天的国家联盟,最后必然上升为联合国——今天的联合国名存实亡,当联合国名存实存之时,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也就建构起来了。当所有竞争的主体都协作为一个整体,自然也就消解了种内竞争。消解了种内竞争就是消解了人类的内耗;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才可能达成统一的文化共识,共同应对人类的系统危机。
王东岳先生的《物演通论》本来是针对既往哲学的遗留问题应运而生的,但在创建了递弱代偿存在论模型、解决了既往哲学的遗留问题后,王东岳先生发现,在论证递弱代偿自然律的同时,就论证了人类文明趋势不良。所以,王东岳先生才说文明是人类的灯蛾之火。在这种趋势下,对科学的正向评价更是加速这种趋势的助推剂,即加速人类史的最后进程。只有明了科学对人类整体存续的巨大戕害,人类才有望完成文化转型,进入后科学、后国家、后资本时代,否则人类就只有暴病而亡了。
也就是说,从“地火”到“天火”就是人类的文明化进程,普罗米修斯开启“地火”其实就是开启这个文明进程,所以,从“地火”到“天火”,只是“链式反应”的必然而已。所以,“天火”只是“地火”的后果,一如今天核战争时刻威胁着人类整个物种的安全只是核弹被发明后的必然后果,核污染深入大海和土壤同样也是核技术被发明后的必然后果。
可见,虽然奥本海默的反思、诺兰的反思在一定范围内是契合了王东岳老师的对于“火”这一象征着科技力量的反思,但反思程度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奥本海默和诺兰对核武器的反思只是基于核武器毁天灭地的摧毁能力,而对核技术应用下持续带给人类的伤害未必有足够的认知,自然也不会展开反思。
就事论事,奥本海默反思核武器,引导观众反思核武器,只是反思的最表层。只有落实到文化层面的反思,才是更深层的反思。在科学时代,人人颂扬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说到底就是怀疑精神和理性,怀疑其实就是对固有认知的动摇,以致于从疑开始打破旧的认知,建构新的认知,但哪怕新的认知,也不是真理,只是代偿层级更多的更武断的认知,因为理性也有其先验规定性,任何理性结论也有其武断前提,换言之,任何科学结论都是有特定武断前提的,公理也是武断前提,一旦前提改变,可能结论就颠倒了。如非欧几何改变了欧式几何的前提条件,整个数学世界都变了。事实上,科学对客观世界的模拟永远是越来越武断的,永远是把一个复杂系统抽象或处理成一个简单系统,才能找到答案。而这个答案,最多是在模拟的某个局部领域达成广义逻辑融洽,其代偿有效性也是局域范围的,而且其有效性的效力注定越来越弱,更重要的是,因为西方哲学没有随着科学同步发展,反而越来越在自身的分化中丧失了追求终极的初始目标和能力,以致于科学时代逐步丧失了哲学,丧失了基于整体领域达成的整体认知,丧失了整体认知对局部认知的约束和反思,而科学对自身的认识往往不够,科学的使用往往无限制或限制不够,以致于把人类急速引入断崖。
所以,人类当下的反思必须要反思主流文化,反思科学本身。波普尔把科学定义为证伪主义已经说明了科学非真,但他因为缺失对于感知方式(即包含了理化感应、感性、知性、理性在内的广义逻辑)最彻底的反思,所以误以为科学可以越来越接近真理,但事实上人类的知识是遵循武断律(也就是简约原理)层层叠加起来的,含真量必然越来越低——包括看起来颠扑不破的数学。等到科学基础理论越来越无法验证时,科学就走到了尽头。现在基本上已经如此了,如十维宇宙只是数学理论的产物,是一个逻辑模型,且永远无法验证,即无法满足科学实证要求,这说明科学在基础理论上已经走到尽头。更不用说,这样的理论是无法通解世界。只有把科学理论视为真理的人才会匍匐在科学理论的脚下,认为科学理论的加持意味着深度和艺术,如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瞬息全宇宙》就是运用新的科学理论编故事,虽然该科学理论本身都无法完成实证和他洽,不足以证实自己的正确性,但一点儿不妨碍创作者和观赏者用来彰显自己带着科学境界的艺术品味和丰富想象力。
更深层的文化反思其实还需要落实到思维方式上,东方的整体性思维天生就没有分化素质,追究的是万物之间的依存关系或衍存关系;而西方的哲科思维追究的是万物彰显的逻辑关系或逻辑形式,精密逻辑更具有持续分化的延展性。虽然后现代哲学也反思了西方表音文字缔造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这种主义下导致的逻辑强迫症,但这种反思只有反对现行文化的解构功能,毫无建构功能,也就只能沦为散乱的文化牢骚。真正能建构新文化的只有在底层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物演通论》。《物演通论》的新思想才能引领人类建构未来新的文明形态。
(三)化竞争为协作
电影《奥本海默》引起我深思还有两件事。
一件是:1939年,物理学家列奥·西拉德(Leo Szilard)和爱因斯坦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警告总统德国可能正在研发原子弹,于是有了后来是曼哈顿计划,但实际上,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德国一直就没有研发和制造原子弹。1945年7月,西拉德发起请愿书,希望杜鲁门总统在使用原子弹前警告日本,爱因斯坦也在请愿书上签名了,可见,西拉德和爱因斯坦的本意并不希望有原子弹这样的大杀器被用于战争,第一次写信给罗斯福仿佛是基于不得不做,但实际上只是基于对德国的妄加揣测。西拉德和爱因斯坦或许都会后悔曾经给罗斯福写过的信。
但这样的过错仿佛也应该被理解,在战争状态、竞争状态下,只有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对方,才会立于不败之地。黑暗森林法则就是基于这样的竞争逻辑产生的。
另一件是:斯特劳斯完全是因为个人的敏感而恶意揣测了奥本海默,才有了后期专门针对奥本海默的有预谋的听证。这最终导致了双方都遗憾的结果。可见,任何不符合事实的揣测往往是害人害己的,但任何人都无法完全脱离这种主观的揣测。避免这种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猜测和轻信自己不在场时别人的言行,哪怕自己在场,也不要把别人的言行先行定义为主观恶意的。人人都难免主观,但人人不可能无缘由的带着恶意,或许自己也不经意间的用不恰当的言行伤害过别人。如果对方无恶意,无需计较;如果对方因为感受到了你曾经无意识的伤害而蓄意报复,更无需计较,否则本来芝麻大的小事会被无限放大,冤冤相报永无宁时。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是一样。坦荡的沟通,消除误会和芥蒂,或者,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以大局为重,都是必要的。
其实,这种恶意揣测源于本能的竞争心理和防范心理,或者说,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深层就是自卑。看奥本海默的传记,前期完全是自恋型、攻击性人格,后期在听证会上反而收敛了攻击性,因为他见识过攻击性文化、攻击性武器、攻击性心理的危害了,但我觉得不攻击的他更强大了。所以,当奥本海默明确德国没有原子弹以后,明确原子弹会无差别的轰炸平民时,明确战争对原子弹的使用没有底限时,明确原子弹乃至氢弹的无限升级的破坏力时,奥本海默反对制造氢弹,这源于奥本海默虽然是科学家,但广泛的涉猎让其思考的东西不仅限于科学,还有印度宗教等广泛的知识赋予的整体思考的能力和本能,所以他更容易反思,而不象泰勒,执着于功名,自始至终都是把制造核武器视为功成名就的手段。
强大不是非要赢、非要在争论中获胜,而是能站在更大的格局下让更多的人和谐相处,和而不同,这才是有意义的交流,也才能达成取长补短的融合。所以,真正强大的文化也不是能缔造原子弹的科学文化、不是单纯能提升必须竞争力的文化,而是能反思科学的在更大的哲学范围统一世界底层认知的文化。在系统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国家之间还以竞争思维、冷战思维相处,是人类共同的悲哀。
对于个人也一样。在当下这个新旧秩序交替的过程中,加上智质分化,人与人之间的认知空前差异化、多样化,世界观、价值观大相径庭的人也经常在不同的视频下互相网暴。实际上,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只有王东岳先生那样的终极评价才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各种情景评价各有各的特定视角下的理,这时候,我一般站在少数人那边,因为越是少数人的声音,越是需要被听见,越是多数人的声音越容易成为简易的暴力。而且,当前的认知和讨论越是流于情景、流于表面、流于特定文化视角或个体经验的局限认知,越需要建构共同的底层认知,越需要《物演通论》这样能缔造共同底层认知的,能建立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哲学理论。因为,文化表层的多样性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的,这就要求文化底层的统一性必须成功建构,否则人类就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凝结成一个整体去应对人类共同的系统危机。
《奥本海默》我看了两遍,影片本身没有任何煽情的内容,但第一次看到最后奥本海默说“我们确实毁灭了世界”时,我控制不住地留下了泪,我很清楚,奥本海默说这句话是基于自己目睹了核弹毁天灭地的攻击力、经历了后续美苏的军备竞赛等事件,但他不明白科学持续的戕害能力远不止这一点,而且,不仅仅是他不明白、导演不明白,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而能让人明白的《物演通论》始终没有站上它应有的位子,获得它应有的荣光,这让人深深地无奈和悲哀,只能焦急、关切又无能为力的看着这个越来越快速趋于失存的世界!
第二次看《奥本海默》再在末尾听到这句话,我只是红了眼眶,无奈和无力的感觉多了,就会麻木一些了,我想我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写了这篇和影片具体内容关系不大的文章。而且,我知道,能看我文章的几百个朋友基本上已经从我以前的文章中明了了我想说的,但真正理解还是需要精读《物演通论》,有些固化认知的改变也需要时间;同时,相对于不关注我文章的人而言,这几百个人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见,一篇文章,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对于这个世界也几乎不会有任何影响。于是,在写了一半又不想写的磨蹭之中,停停写写,最终还是把它写完,也算对自己说过要写影评的交差吧!
最后,附上《知鱼之乐》中《普罗米修斯的天谴词》一文的结尾,是作者代宙斯拟的一份普罗米修斯的判决书或天谴词,实际上,奥本海默比普罗米修斯的“犯罪”情节更严重——
“罪神普罗米修斯,狂悖无知,蔑视天庭,罔顾天下苍生柔弱,惟图私自一时之快,竟将火种流传人间,致使后患再难杜绝。赐火于人,一如献鸩止渴,从此必令人智佻巧,人性轻狂; 凡心激荡,燥气浮嚣; 物欲泛滥,尘寰扰攘; 战端遍地,血腥冲天; 能耗加剧,生计日艰; 文明如泻,社会动摇。终而至于天地污染,雨酸水臭; 军备升级,核武高悬; 怪魔克隆,毒菌弥漫; 生灵涂炭,万物灭绝。呜呼! 宇宙最美好的造化——生态系统; 哀哉! 众神最喜爱的玩伴——人类世系; 就此均被付之一炬。念之令吾痛断肝肠。如此恶果,无异于捣毁世界之精华! 如此罪孽,凌迟不足以惩戒其万一! 故此特命施以天庭最酷烈之刑罚,镣铐山崖,剖腹暴肝,百鹰竞啄,食而复生,如是永无休止,以傲效尤。钦此。”
——虽然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在时代背景下没有上帝视角(上帝视角其实就是哲学追求终极的整体视角),做时代追捧的事更是理所当然,无所谓“罪”;但整体的彻底的反思本身就包括了对人类每个时代的反思以及每个时代的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反思!反思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向未来!
